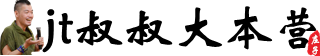辅导查琳的那一段期间,我对于根本的人性之恶,一无所知。在我的专业知识领域内,没有邪 恶这样的词汇,也从不曾接受以邪恶为主题的训练。对于精神医生或是任何一位学科学的人,邪恶 不是公认必须探讨的领域。我一直被灌输的观念是,精神病理只能用已知的疾病或精神力学来诠释, 而且标准版的心理异常诊断统计手册(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均会将精神病理加以适当 命名,并收录于书册之内。我竟然未将美国精神医学界全然忽略了人类意志中此一基本的本质,视 为不可思议的事。不曾有人向我讲述类似查琳之类的个案,因此让我对于如何辅导查琳,感到措手 不及,如婴儿般的无助,丝毫不知如何因应。
查琳的个案让我不经一事,不长一智。毋庸置疑的。她引燃我写本书的动机。
相对于探知人性之恶的迫切需要而言,这些年我从查琳身上所获致的心得,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 如果有机会让我重新再辅导查琳,我将会以截然不同的方式来处理,相信结果应会令人满意。
首先,我会以更敏捷的速度及更自信满盈的态度,探究查琳个案中所包藏的邪恶。我不会受强 迫型精神官能病症的误导,误认为所处理的个案是一般的精神官能症,或是受查琳的自闭症所误导, 怀疑自己是否发现了精神分裂症的怪异变体;我不会陷人九个月的傍徨困惑期,或是投入一年多的 时间往恋亲情结的方向,做无用的诠释。直到最后,当我将查琳根本的问题归属于为邪恶时,我仅 能以试验的性质进行疗程,毫无权威感可言。我不认为应该用蜻蜒点水的方式来诊断邪恶6除此之 外,当时我所归纳出带有实验性质的结论,均在后来一一得以肯定。如果必须再重新辅导查琳,用 不着三年,只消三个月我便能发现查琳的问题症结,也有信心能够治疗她。
我会先从我的困惑感开始追溯。现在,我已经了解,激起他人的疑惑困扰是邪恶的特征之一。 在开始辅导查琳的一个月,我便已经察觉自己充满了困惑,但我却臆测是自己太不聪明,才会感到 困惑。在疗程进行的第一年,我从来不曾认为我之所以困惑重重,是因为查琳想要困扰我,但是换 作今天,我就会作如此大胆的假设,然后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加以求证。若果真如此,那么便能很 快展开诊断。以这样冷静的方式来处理查琳的个案,会不会因此逼得她退出治疗?显然不无可能。
首先,我要问查琳为何前来进行治疗?从她口中道出想要寻求协助的原因,已不可考,反倒是 她所显露出想要玩弄我、引诱我的企图,昭然若揭。其次,我必须问她为何尽力接受长期的治疗? 答案似乎在于我让她产生再继续玩弄的兴致,也让她继续抱持有朝一日终能够引诱我、拥有我或征 服我的希望。最后,我还必须问,查琳为何不愿再接受治疗?最显然的原因应该是,当我逐渐掀开 查琳的底牌,她愈来愈察觉出无法引诱我;能够将我玩弄于股掌的空间,也愈来愈有限。
如果我在疗程初期即明白真相,不但察觉出查琳的邪恶,也具备与邪恶对抗的力量,那么查琳 极可能早就高举白旗,放弃这场根本赢不了的会战。话虽如此,查琳继续接受治疗的几率仍是存在 的。
我认为查琳并非邪恶得无可救药,我们必须牢记,恶人几乎不可能会委屈自己接受精神治疗的 洗礼,让自己相形见细。查琳之所以愿意担此风险有可能是因为她一心想要击垮我;也有可能因为 在她内心的某一小部分渴望被救助;或是因为她不是属于穷凶极恶的类型。事实上,上述的可能性 皆可能同时存在口人常有一体两面一一至少某些恶人往往是处于矛盾冲突的心态中。而我对于查琳 之所以想要接受治疗,首要的假设是,她既想要征服我,又想被拯救。
只是,查琳的征服欲似乎稍强一些。然而,如果我以更具智慧的态度来面对查琳.她是否会任 由自己被征服一一也就是为了赢得她的灵魂而投降?这牵涉到威权的问题。在过去这些年中,我发 现恶人格外地服从威权,我不知道原因何在,我只知道此一现象确实存在。
我必须强调,凌驾恶势力之上的威权力量,非比寻常。除了得以知识做后盾之外,还得使出庞 大的力量才能获得,而这股力量仅能凭爱而生。辅导查琳时,我的确具有这股爱的力量,只是因为 知识不足而失效。如今我已经掌握了知识,如果再有机会.我仍将乐于辅导查琳,只是我对于必须 投注那股巨大的能量才足以成事,禁不住打了个寒战。
真爱的本质是牺牲与奉献,以往我从来不曾具备与查琳的邪恶正面交战的信心.但如今我了解 如欲真正地与邪恶交战,则必须有面临心力交瘁至无以复加的心理准备,也许伤口甚至永远无法痊 愈。所以,换作是今天的我,则会迅速挟着凌驾于查琳之恶的威权,加以因应。此外,基于此一新 发现,我会尝试直接道出查琳内心的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