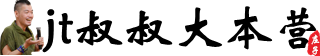虽然许多专业书籍,对于反移情作用的主题着墨颇多。但却独缺反感反移情作用的描述。有数 点原因可以解释:第一,反感反移情作用与邪恶的关系,非比寻常,几乎无法只提其一,不提其二。 第二,邪恶被精神治疗研究视为洪水猛兽,要诊断常会不得其门而入,因此这种特定的反移情作用 也不例外。其次,精神科医生多半悲天悯人,若表现出如此激烈的负面反应,往往损及自我的形象。 第三,基于这种强烈的负面反应,精神科医生多半避免与邪恶的病息建立长久的关系。最后一点, 正如我先前所述,极少数的恶人愿意接受精神治疗。除非情况特殊,否则他们宁可想尽办法逃避这 种心灵点灯light-shedding的治疗过程。于是,医生一直难有充裕的时间与恶人共同探讨他们的 反应,或是观照本身的反应。
邪恶时常使人产生另一种反应:迷惑。曾有一名女子描述碰到恶人时的感觉:顿时之间我好像 丧失了思考能力。面对邪恶就是会产生这种困惑感。恶人自欺欺人;一面编织层层自欺的谎言,一 面欺骗他人。诊疗医生的困惑若因病人而起,则必须质疑是否因为本身的疏失所致。但是医生也有 必要问:可不可能因为病人做了什么事,而使我困惑?我在第四章所描述的个案,就是因为未思考 这个问题,所以一筹莫展了几个月。
先前我曾经提出,反感反移情作用是面对恶人的适当反应一一甚至是免食恶果的反应。惟一的 例外是,诊疗医生只有在洞悉困惑,且对于所处的现况成竹在胸,但仍决定与恶人建立诊疗关系的 前提下,才应该而且能够将反感反移情作用置于一旁。前述条件必须配合,反感反移情才告成立。 治愈恶人的企图心,绝不应如蜻蜒点水般的淡然,必须拿出惊人无比的精神及心灵力量。
处于全力以赴心态的诊疗师之所以能够如此义无反顾,不仅由于恶人让人畏惧,也因为他们令 人同情;他们长此以往不愿自我曝光、不愿倾听良知的告白,他们是最对人类生惧、全然生活于恐 惧中的人。恶人根本无须被打入任何一层地狱,他们已经置身于人间的炼狱了 !
因此,不仅为了社会,也为了恶人,医生自应竭尽所能帮助恶人挣脱出人间炼狱。只是目前, 我们对恶的本质所知有限,缺乏诊断的技巧。然而,正由于我们尚未发现邪恶是一种特异的疾病, 因此诊断上的拙处,也就隐而不彰。本书旨在阐述,邪恶可以被定义为某种心理疾病的特定形式, 我们至少应该像关注其他重大的精神病一样,以科学的态度探讨邪恶。
在一般的情况下,勇闯虎穴是合情合理的明智之举。如果我们能将恶视为一种病,尽管依旧充 满危险,但其情可悯,并且明了一切的应对之道,那么为了建立治疗关系,我们应该化反感为谨慎 适度的慈悲心。
经过了二十年,再回顾巴比与其父母的个案,我不认为即使现在的我已累积了多年的临床经验, 处理的方式会大异其趣。我仍然认为,将巴比从父母的身旁拯救出来,是首要任务。我还是会和当 时一样,运用世俗权(temporal power)完成此项任务。二十年来,除了原始力量之外,是否还有其 他事物迅速对恶人发挥影响力,我依然没有新发现。不论是宽大为怀的对待,或采取任何一种我所 熟悉的宗教形式,恶人一概相应不理一一至少短期是如此。但有一点和二十年前不同:如今我知道 巴比的父母是恶人,当时我并不知晓。我感觉出他们的恶,但说不出为何物。我的指导医生无法协 助我认清我所面临的情况;因为恶并不存在于当时的专业语汇之内;这是因为我们是科学家,不是 传教士,不应该用这些语汇来思考。
会诊巴比的父母时,我全然不知与自己斡旋的是哪一种力量。我讨厌它,对它一点也不好奇。 我不想与巴比的父母打交道,不仅因为对于该力量心存敬重,更因为对它望而生畏一一莫名的恐惧 a如今我仍然有所惧,但不再是盲目地恐惧。得知力量的名称后,我对它的来龙去脉稍能掌握。由 于我秉持的立足点稳若磐石,我承受得起对它的本质产生好奇;我能承担迎向它的后果。所以如今 我的因应之道,可能与过去大相径庭。如果今天我有机会,在让巴比成功迁出父母家之后,我会用 最模棱两可的说辞委婉告知巴比的父母,被一种具有毁灭力量附身的人不止是巴比,他们自己也是 —样。倘若时间及精力允许,我会提出建议,与他们一起合作,试图将那股力量征服。如果他们同 意我的提议,我就会着手与他们一起进行一一并非因为我现在对他们比较有好感,也不是因为我对 于治愈他们有十足的把握一一而是因为获知恶的名称之后,我变得坚强,能够秉持学习及尝试的心 态,投入其中。而在我们所熟知的领域,全力以赴,是义无反顾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