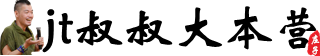- 但是
- 以一个心理分析的角度
- 我们就会明白
- 重要的是
- 他的心理结构
- 没有办法「容许」、「谅解」任何跟他人生观不一样的人
- 他做不到──即使他「自我要求」的道德观之中有一条是「人要原谅、要宽以待人」
- 他也做不到──他只能假装不在意
- 其实还是很受不了的
- 自律极其严苛的人
- 如何能够宽以待人
- 一个真心相信「不信我的神的人
- 会下地狱被烈火烧到永恒」的人
- 如何能够坦然地去爱、去接受不信他的神的异端者
- 心理基盘已用「极严厉的人生观」制造出大量的罪恶感和羞耻感
- 而一路都用罪恶感和羞耻感作为动力
- 恐吓、逼迫自己以「他认为正确的道路」活到今天的人
- 他眼中的别人
- 只要和他观念不同
- 他大约都只能看到罪人、看到不配活在世上的人
- 而这样的人
- 如果有伴侣
- 而他的伴侣又是他的标准中「不够合格的人」的话
- 他是用什么样的心情在拥抱、亲吻他的伴侣的
- 是不是很有可能在心中无奈地默默叹了一口气……
- 他在伴侣身上看到的诸般不合意的种种
- 他表现出来、或硬吞回去压抑的「指责」的情绪
- 无论如都会让他的伴侣感觉到「跟这个人相处空气好沈重、超有压力的」
- 而
- 伴侣之间
- 一旦有了这种压力
- 自律神经就卡死在交感神经这一边
- 性生活的质量
- 自然也就乏味、惨烈之极
- 有不如无了
- 我前一阵子常说一句话
- 性这个东西
- 必须是把人当作人看待时才能成立的
- 如果我们把自己搞成了一个十分严厉的正人君子
- 往往
- 在不自觉之中
- 对别人是有很多「苛求」的
- 而这些要求
- 变成了我们判断他人的一种审查标准之后
- 我们就会好像在菜市场挑西瓜、挑萝卜一样地在评估「对方够不够资格成为我的伴侣」
- 我们会变成一个审判者
- 可是
- 一旦我们把人当作西瓜、萝卜一样地看待、挑捡时
- 我们的性生活质量
- 就真的会降低到好像在强奸一颗西瓜、一根萝卜一样乏味了
- 因为
- 到底
- 我们所经验到的「实相」
- 是我们自己内在的心理结构投射出去的能量所形成的
- 所谓的「把人给物化了
- 是一种对人的贬低」这么一种说法
- 与其用来指那些色情图片上的麻豆
- 不如说
- 有更多的正人君子
- 是在如此地不自觉之中
- 用一重又一重的严格审核标准
- 也把人给物化了──只是美其名曰
- 「我是希望你能更好
- 」然后
- 性的价值
- 就被这些「把性搞坏成垃圾的人」给贬低了
- 也是说
- 人类在涉入性活动之前的「求偶活动」
- 所作的「为自己的吸引力加分」的种种努力
- 常常是一个不小心
- 反而让自己变成了一个无法享受性活动的人
- 更直白无味的说法
- 性的美好
- 在于提振副交感神经
- 但
- 如果一个人
- 一天有百分之九十五的清醒时刻
- 都在给交感神经增压
- 养成了只在给交感神经增压的习惯
- 就算有了性活动
- 这个人只怕也是积习难改
- 扭转不过来了
- 可是
- 这些把性的功用都搞坏了的人
- 偏偏又是比较有性欲、比较在受性欲虐待的人
- 因为
- 对自己诚实的真小人
- 他的交感神经不太紧张
- 所以他的性欲是淡淡然很温和的东西
- 但这样的人
- 如果从事性活动
- 性生活的质量却是相对美好的
- 有快感、有疗愈的效果
- 而这些交感神经超紧张的人
- 他的性欲通常也是极其猛烈的
- 但是
- 他的性行为质量
- 反而是一种没什么快感、只是把自己搞虚掉的纯发泄
- 而他如果一直反覆经历这种「被性欲煎熬
- 然后
- 忍不住做了
- 又觉得好后悔、好自责
- 因为又不开心、又空虚
- 觉得自己像笨蛋一样」的过程
- 是不是很有可能
- 他会对性的看法越来越负面
- 对这样的自己越来越痛恨、恼羞
- 而终于会说出象是「万恶淫为首」之类的话
- ──不想觉得「恶」的是自己
- 索兴把所有的「恶」都推到性的头上去算了
- 可爱的人
- 如果要说一个清楚的定义
- 让我们家莹莹来说好了(因为她的性生活质量相对美满
- 所以她说了算)
- 有一次莹莹在感概她的人生实在是太幸福──这对男女
- 就喜欢乱发这种闪光文
- 「我性生活超美满
- 你完全不懂这有多快乐
- 」之类的──有一天莹莹说了一句对她男朋友丁助教的评价
- 「叔叔
- 我觉得我很幸福的一点
- 是有丁这样一个人
- 他看到了我所有的缺点
- 却愿意包容我、等待我、提醒我
- 我内心自己都觉得很可怕、丑陋的黑暗面
- 都敢在他面前表现出来
- 」其实
- 这句话就够了
- 你愿意做一个
- 能够看到对方所有的缺点(并不是当一个瞎眼的白痴)
- 但是不用你头脑里面的「应该」去打压对方
- 让他尽情地做自己
- 信赖他终会找到自己生命的呼唤
- 如果你能够变成如此可爱的人
- 任何人跟你相处的时候
- 他没有秘密
- 他觉得什么话都可以跟你讲
- 因为你不会谴责、批判他
- 所谓不可爱的人
- 就是心里面「规矩很多」的人
- 跟他相处
- 你会知道
- 「如果我表现得懒惰一点
- 他会瞪我
- 如果表现得贪玩一点
- 他会骂我……」很多人心中是有很多规矩的
- 别人跟你相处的时候
- 你的规矩越多
- 对方就越有压力
- 越有压力
- 就越不能启动副交感神经
- 所以
- 如果两个人都能够完全包容他人
- 接受人是不同的
- 每个人有自己生命的呼唤
- 我不能强求一样的标准
- 看到任何人、任何事
- 都能够包容、能够接受、能够欣赏
- 人家跟你相处时
- 感觉不到你的任何谴责和压力
- 如果有两个如此可爱的人
- 而他们在肉体上又互相吸引的话
- 他们的性
- 就可以达到修道的高度
- 这是一个非常难有的机缘
- 但并非不可能
- 我想
- 我今天的报告就可以在这里结束了
但是,以一个心理分析的角度,我们就会明白,重要的是:他的心理结构,没有办法
「容许」、「谅解」任何跟他人生观不一样的人!他做不到──即使他「自我要求」的道德观之中有一条是「人要原谅、要宽以待人」,他也做不到──他只能假装不在意,其实还是很受不了的。
自律极其严苛的人,如何能够宽以待人?一个真心相信「不信我的神的人,会下地狱被烈火烧到永恒」的人,如何能够坦然地去爱、去接受不信他的神的异端者?
心理基盘已用「极严厉的人生观」制造出大量的罪恶感和羞耻感,而一路都用罪恶感和羞耻感作为动力,恐吓、逼迫自己以「他认为正确的道路」活到今天的人,他眼中的别人,只要和他观念不同,他大约都只能看到罪人、看到不配活在世上的人。
而这样的人,如果有伴侣,而他的伴侣又是他的标准中「不够合格的人」的话,他是用什么样的心情在拥抱、亲吻他的伴侣的?是不是很有可能在心中无奈地默默叹了一口气……?
他在伴侣身上看到的诸般不合意的种种,他表现出来、或硬吞回去压抑的「指责」的情绪,无论如都会让他的伴侣感觉到「跟这个人相处空气好沈重、超有压力的」。
而,伴侣之间,一旦有了这种压力,自律神经就卡死在交感神经这一边,性生活的质量,自然也就乏味、惨烈之极,有不如无了。
我前一阵子常说一句话:性这个东西,必须是把人当作人看待时才能成立的。
如果我们把自己搞成了一个十分严厉的正人君子,往往,在不自觉之中,对别人是有很多「苛求」的。而这些要求,变成了我们判断他人的一种审查标准之后,我们就会好像在菜市场挑西瓜、挑萝卜一样地在评估「对方够不够资格成为我的伴侣」。我们会变成一个审判者。
可是,一旦我们把人当作西瓜、萝卜一样地看待、挑捡时,我们的性生活质量,就真
的会降低到好像在强奸一颗西瓜、一根萝卜一样乏味了!
因为,到底,我们所经验到的「实相」,是我们自己内在的心理结构投射出去的能量所形成的。
所谓的「把人给物化了,是一种对人的贬低」这么一种说法,与其用来指那些色情图片上的麻豆,不如说,有更多的正人君子,是在如此地不自觉之中,用一重又一重的严格审核标准,也把人给物化了──只是美其名曰:「我是希望你能更好。」
然后,性的价值,就被这些「把性搞坏成垃圾的人」给贬低了。
也是说,人类在涉入性活动之前的「求偶活动」,所作的「为自己的吸引力加分」的种种努力,常常是一个不小心,反而让自己变成了一个无法享受性活动的人。
更直白无味的说法:性的美好,在于提振副交感神经。但,如果一个人,一天有百分之九十五的清醒时刻,都在给交感神经增压,养成了只在给交感神经增压的习惯;就算有了性活动,这个人只怕也是积习难改,扭转不过来了。
可是,这些把性的功用都搞坏了的人,偏偏又是比较有性欲、比较在受性欲虐待的人。因为,对自己诚实的真小人,他的交感神经不太紧张,所以他的性欲是淡淡然很温和
的东西,但这样的人,如果从事性活动,性生活的质量却是相对美好的;有快感、有疗愈的效果。
而这些交感神经超紧张的人,他的性欲通常也是极其猛烈的,但是,他的性行为质量, 反而是一种没什么快感、只是把自己搞虚掉的纯发泄。而他如果一直反覆经历这种「被性欲煎熬,然后,忍不住做了,又觉得好后悔、好自责,因为又不开心、又空虚,觉得自己像笨蛋一样」的过程,是不是很有可能,他会对性的看法越来越负面,对这样的自己越来越痛恨、恼羞,而终于会说出象是「万恶淫为首」之类的话?
──不想觉得「恶」的是自己,索兴把所有的「恶」都推到性的头上去算了。
可爱的人,如果要说一个清楚的定义,让我们家莹莹来说好了(因为她的性生活质量相对美满,所以她说了算),有一次莹莹在感概她的人生实在是太幸福──这对男女,就喜欢乱发这种闪光文:「我性生活超美满,你完全不懂这有多快乐。」之类的──有一天莹莹说了一句对她男朋友丁助教的评价:
「叔叔,我觉得我很幸福的一点,是有丁这样一个人,他看到了我所有的缺点,却愿意包容我、等待我、提醒我。我内心自己都觉得很可怕、丑陋的黑暗面,都敢在他面前表现出来。」
其实,这句话就够了。你愿意做一个,能够看到对方所有的缺点(并不是当一个瞎眼的白痴),但是不用你头脑里面的「应该」去打压对方,让他尽情地做自己,信赖他终会找到自己生命的呼唤。
如果你能够变成如此可爱的人,任何人跟你相处的时候,他没有秘密,他觉得什么话都可以跟你讲,因为你不会谴责、批判他。
所谓不可爱的人,就是心里面「规矩很多」的人,跟他相处,你会知道:「如果我表现得懒惰一点,他会瞪我;如果表现得贪玩一点,他会骂我……」
很多人心中是有很多规矩的,别人跟你相处的时候,你的规矩越多,对方就越有压力, 越有压力,就越不能启动副交感神经。所以,如果两个人都能够完全包容他人,接受人是不同的,每个人有自己生命的呼唤,我不能强求一样的标准。看到任何人、任何事,都能够包容、能够接受、能够欣赏,人家跟你相处时,感觉不到你的任何谴责和压力。如果有两个如此可爱的人,而他们在肉体上又互相吸引的话,他们的性,就可以达到修道的高度。
这是一个非常难有的机缘,但并非不可能。我想,我今天的报告就可以在这里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