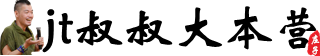如果『荣华』我们不解释作面子,而解作『名利』,状况也还是差不多: 好比说,有学术圈的前辈,长年是要向政府单位申请研究经费,老在写『把
自己的研究吹嘘得好伟大、对人类好有贡献』的那种企划书的让你,你听他讲话,往往会吃惊:『为什么一个人讲话含金量可以这么低?扯了两个钟头,一个重点都没有!』
如果要多说一两句,等同『面子』波长的念波,还有一个『紧张』:
有次我在一家店买外带的章鱼烧,那个店员,满头大汗,慌慌张张,我前面排了两个客人,第一个客人,他给装错了;第二个客人,他又装错了;到了我,他还是装错了!我想前面那两个客人和我,大概都在皱着眉头想:『这人有病是吧?』我看着他慌张得焦头烂额的那个样子,我忽然想通了:『这是passive-aggression!』
他表面上是紧张,他自己也以为他是紧张,但事实上是,他就是存心要虐每一个人!只是他动『紧张』这个情绪,他就可以『我没有这个意思』地把自己的恶意都否定掉了。紧张的背后,真是的恶意是搞破坏,只是你有紧张作为伪装,别人就不好直接指责你的敌意了。所以这个念波,还是像面子一样,很容易把人直接拖向解离;比直接的『我没有这个意思』还要更奸诈。
不过,另外还有一种紧张是正能量,那是『高度专注到都不出错』的心力贯注的状态,那会让人进入无时间感、无自我感,是达人之心的状态,和我哲理举的例子是不同的;姑且说明一下。
2019 年 6 月 30 日星期日
故有儒墨之是非。庄子说,因为大家为了面子,名利,讲话都歪掉了,对于真相的要求也都不高,于是,中国就变成儒家跟墨家可以打架、可以互相批评的地方了。
实际上墨家有点象是周朝的嬉皮族,他们追求自然、简朴的生活,要求对别人有平等的爱。这听起来是不是很好?
儒家就是要求人要为了社会秩序,一定要把人的分位做得很安稳,大家都安于本分,贡献自己的心力,让这个社会能够大家一起同心协力、发光发热,这听起来都是很好的。
可是,庄子对于儒家的批评,就讲得很清楚:『负面心想事成大法』;你所有的那些口号、教条,都是你不相信人会好起来才说的。同样是儒家,到了孟子——庄子跟孟子同一个时代,但他们两个好像从来没见过面——儒家才出现第一次的反省。
孟子的主张,就不是负面心想事成大法。孟子是这样的:一个国王朔:『我没办法行仁政,因为我很好色。』孟子说:『好色很好啊!肉体享受是很快乐 的事情啊!你既然好色——什么事情都是这样,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与 少乐乐,与众乐乐,孰乐?你自己爱吃牛排,有人陪你吃牛排,你就会更开心 对不对?——你就在全国办理婚友社什么的,让全国人民都享受幸福的性生活, 国无旷男怨女,这样大家都觉得你好好,这就是仁政!』
孟子不跟你逃避黑暗面;你有黑暗面,我们就来发扬光大一下,让它价值完成,就光明了。孟子对儒家做了第一次的反省。
但是在庄子、孟子之前的时代,儒家还是非常小心的。所以庄子透过一些角色批评孔子。他说:『孔子啊!最狂信你的死忠粉丝弟子是子路,可是你看子路死得多惨!』子路这个橘色,因为他只相信老师说的人生地图神圣的真理, 他自己走路是不看路的,所以他叫子路?简直撞电线杆的专家。
<齐物论>后面有个地方,庄子对孔子的师徒关系,提出了一个很微妙的批评:
『如果你以教就会,老师其实不会高兴。』你懂我意思吗?像我这种中医,有徒儿青出于蓝,我高兴吗?其实有点心酸酸。但是,如果你怎么教都不会,老师觉得『你辜负我的苦心』,也不会高兴。老师作为教主本身,一个超矛盾的存在。你知道那种奇怪的感觉对不对?
中国人会觉得,『师徒制』就应该怎么样怎么样,师徒之间是一种伦常关系。但道家的观点,你看庄子的世界就会知道,《庄子》书中的徒儿们,都是爱怎 幺冲撞老师就怎么冲撞老师,爱怎么噎老师就怎么噎老师的,他的徒儿都是很 野的。
儒家建立一个很有规范的礼教系统,我们中国的师徒制,多说是从这个系统来的。相信各位对于师门里要如何『执弟子之礼』,一定略有耳闻,否则哪能得到师父的真传,是不是?
老实说,身为中医人,如果我是一个某某神医,我真的希望我的徒儿功力跟我一样好吗?这很难说。我没有说『一定不』,但问题是,你可能不会真的很希望徒儿跟你一样好。我有一个同行,他的爆炸点就是『我也会』。当他在那边洋洋自得、自夸自己多大本事的时候,我跟他说:『这,我也会。』他就差点气炸掉。
你引以自豪的独门本事,人的自我,真的不希望别人也会;但人家『不会』也不行:『我教你那么久,你怎么还不会?你辜负我!』
所以『徒儿』本事就是一个非常为难的角色。这不是道家书上讲的,是儒家书上讲到孔子跟颜回之间的事——颜回是孔子最得意的弟子——颜回跟孔子关系的微妙之处在于:颜回死了之后,孔子大为伤痛,大叹道法后继无人,因为颜回是他仅见的天才儿童……有这个故事,对不对?可是,如果孔子真的爱颜回,当颜回面有菜色的时候,他就会说:『乖徒儿,来老师家吃饭啊,师母刚好蒸了馒头。』才对啊,结果连这个都没有!
庄子就拿这个来借题发挥了。在<人间世>那一篇,孔子叫他持斋,颜回跟老师说:『我已经饿那么久了,很斋。』他们师徒关系很奇怪,好像孔子爱颜回爱得不得了,又好像孔子非要这个人死——就是那种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