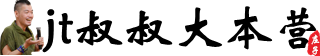我不是说佛教完全没有可行的技术哦!禅宗、或天台智顗(yi 三声)大师都曾发现过可行的操作方法,只是目前一般普罗大众的佛教世界,比较欠缺可行的技术。
我们练习道家的人,就会经验到:我只要找到事实,这个情绪就会消失,我的确可以不愤怒、不恨人,可以不痛苦,可以不要活在罪恶感跟恐惧之中…… 只要顺着这个技术,就确实可以操作到。
但若没有这个技术,就会变成:强迫自己『不要贪嗔痴、不要恨人、要充满慈悲』什么的,会变得很勉强地,把佛法修练成一种『扑灭心中之神、朝向解离迈进』的努力。
站在修练操作的角度,我是这样看的:并不是要反对佛法,而是觉得,借着道家的训练,你确实掌握到承认事实的技法了,你才能有效地做到佛法的修行。
因为,佛教在中国放了一千多年,却没什么人做得到『感知得正确』这件事, 连最基本的第一招都没有人做到过,于是,信众也对这八正道的起手式,渐渐 失掉热情了。
比如现在台湾佛教界,讲到八正道的第一道,就说:『正见,就是要相信, 只有佛法是对的。』原来非常直白的『感知正确』这件事,就被扭曲成:『你要当我们家的狂信徒。』这样,修佛法就没有起跑点了。
我觉得各个门派的训练,都有它指向性的意义。我会选择道家,是因为道家有一个可操作的起跑点:其他,我就觉得有些可操作的技术有点太过暧昧,或者太过艰难,或者一开始就把结果(慈悲)当成修炼法(感知得正确)。
我练道家练到今天,越来越不会有情绪,也的确常常觉得,我内心很安定。但,那是结果,不是过程。
如果我没有经过『寻找真相、消除内在谎言』的过程,而是在那边打坐、调匀呼吸,让自己的内心不要有杂念,然后再遇到原来会让我生气的事,我就真能不生气了吗?——我是绝对有点不太肯定耶?
而我也刚好认识有在练习调息打坐、不要有杂念的人;结果,遇到事情,他还是照样很气——所以,或许这两者,其实是不同向度的事情?
前一阵子,有个小插曲:我们有个一起吃饭摊钱的那种酒肉朋友,我们姑且叫他阿信好了。男生,但是像日本连续剧《阿信》一样,是比较苦命的一个男生。有一天我们一起吃饭,阿信就说,一年前,他跟朋友约好了一起去东京哪里玩,然后那朋友在东京临时说,同行的另外一个朋友比较需要照顾,要阿信自己去玩,他去照顾那个朋友。阿信觉得被人家放鸽子,很受伤、很委屈。
听到阿信抱怨,郭秘书和天威就有点愣住,说:『这种事情会让你难过吗?』我们一下子还没有足够的同理心。
阿信就说:『对啊!人家跟你约,然后放你鸽子,这当然会难过啊!』然后郭秘书就很亲切地问他说:『你是日本不认识路,所以没有他带,你就去不了了吗?』他说:『不会啊,我自己就去了。』天威再问:『那你去了,就去没
有玩到吗?』他说:『有玩到。』我们就追问:『那你损失了什么?那个人是 你很爱、很爱、很爱的人,所以你是感情受伤了吗?』他说:『也没有那么爱, 根本也不太熟。』阿信说:『可是……人,就是应该守信用啊!』
过了一阵子,我又跟阿信吃午饭,只见他叹了一口气说:『你那天在家里放那个玉置浩二唱的<你别走>(张学友的<秋意浓>的原曲),结果我昨天上班的 时候一直哼这首歌,同事还觉得我很开心。其实我是很哀怨的,因为我们公司 有个同事受伤了,结果我的老板居然说:『我只在乎明天有没有人来上班啦!』人家受伤了,他还这样讲,我听了之后非常受伤,整个下午都很不高兴。』
我听着,表情有点窘迫,阿信说:『谭老师,你听我这样讲,是不是绝对我很烦呐?』
我说:『我感觉到的为难之处,不是『烦』,而是……』——因为阿信是常常会说『你应该要怎样』的那种人——『……我只是觉得,好像从上次吃饭到 这次吃饭,你里面有很多的『应该』:老板『应该』要关怀员工,朋友『应该』要守约陪你去哪个游乐场。这些『应该』的设定如此之多,地雷埋得满满的, 谁走过去,都难免会踩爆几个,然后你本人就被炸得乱七八糟。』
当然,阿信也不是什么要练《庄子》的人,就说:『算了,不跟你讲啦。』但我觉得,当你练《庄子》练熟了,你对自己的地雷可以埋哪里、可以拔掉
哪根,有自主权的时候,你看到别人因为有那么多的『应该』而痛苦,真的就是这种愕然的感觉。
我们待会要讲的修练的第一点,就是『消除是非心』;要变成没有道德上的善恶、但是有科学上的因果的人。你很清楚『怎么做、会有什么结果』就好了, 不必讲道德上的善恶。
讲道德上的善恶,就会像阿信一样,每天被自己的道德炸伤。2020 年 2 月 17 日星期一
<逍遥游>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
《齐谐》者,志怪者也。《谐》之言曰:"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 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 天之苍苍,其正色邪?其远而无所至极邪?其视下也,亦若是则已矣。
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覆杯水于坳堂之上,则芥为之舟。置杯焉则胶,水浅而舟大也。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故九万里则风斯在下矣,而后乃今培风;背负青天而莫之夭阏者,而后乃今将图南。
蜩与学鸠笑之曰:"我决起而飞,抢榆枋,时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适莽苍者,三餐而反,腹犹果然;适百里者,宿舂粮;适千 里者,三月聚粮。之二虫又何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