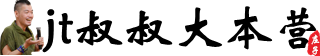偶尔我们会选择一所高中进行“创造技能”的实验课程。我们要求学生列出自己想要的事物。通常学生们想要的都是结果,例如:“工作”、“男女朋友”、“吉他”、“机车”,有时候则是“好成绩”和“改善与师长关系”。
在修习这门课之前,这些学生师长们灌输一个观念:他们无法创造自己所要的事物。而他们也都有好多无法创造的经验。如果你到课堂上,试图让学生相信他们可以创造自己想要的生活,他们会迫不及待地证明你是错的。想要改变这种态度和观点似乎不太可能。
这些学生的观点早已根深蒂固。他们不具备任何创造自己所欲的经验,当然也就不相信自己具备这种能力。此外,他们也很少眼见成人能够创造自己所欲。而这些成人正好是那些动不动就喜欢耳提面命一番的人。
课程快结束时,学生们开始了解自己拥有创造能力,因为他们已经有了创造的经验。他们当然没有服用任何兴奋剂。而他们的能力也不止于作出这样的结论:
“你是否创造了这份工作?”
“是的。”
“你是否创造了这份关系?”
“是的。”
“你是否得到了想要的机车?”
“是的。”
“你是否创造了与父母间良好的关系?”
“是的。”
“你的分数是否提高了?”
“是的。”
在上述一连串经历后,这些学生发现了两项重要的事实:一、他们能够创造自己所选择的事物,二、他们所要的事物并非微不足道。
即使这些学生的目标对全人类而言并无助益,但这又怎么样呢?重要的是,他们创造的东西对他们重要就好了。他们是这么爱他们所想创造的东西,以致非将它们实现不可。臆测别人想要什么东西是一件事情,实现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又是另一件事情。
创造经验改变了这些学生的生活。如果就世界的标准来看,创造的事物并不重要,那么重要的,应是创造过程的事实与能力。从此,这些年轻人不必再过妥协的生活。事实上,他们现在更能发挥心中的利他主义。这种利他主义并非出于”行善“的义务,而是出于真正的愿望,出于对事物的热爱。
天底下仍有新鲜事!
汽车、电话、电视机、太阳反射器、太空梭等现代文明的产物,在以前不但不存在,而且连听都没听过。
对古时候的人而言,摇滚乐、饶舌歌、甚至连古典音乐,都是毫无意义的名词。两百年前,也并无所谓的社会学、人类学、化学、核子物理学,但是今天这些学科都已有了良好的基础。另外,近十年来的科技发展改变了整个世界,这在二十年前是绝对想像不到的。
当作曲家创作时,摊在面前的只是一本笔记本。当画家开始作画时,眼前所见只是一张空白画布。有时候人类实在很难想象一个从未存在过的事物,怎样才能被创造成形。我常听人家说,“这不算什么新奇的事物”或“这件事情左右人做过了”。我倒要问问这些人,贝多芬的第一三三号作品在完成之前,是否就有类似的作品存在了。
事实上,当时的四人先乐团从未见过类似的曲目。有些弦乐团甚至表示这种曲目恐怕难登大雅之堂,因为它不但不好演奏而且难以入耳。有些音乐家第一次见到这个曲目时,认为步入老年的贝多芬是不是已经丧失了稳定性。但贝多芬却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自己的作品,他说:“这首曲子是为以后的人编写的。”而今天,大多数的四人弦乐团都已将此一曲目纳入基本演奏中。
艺术界和科学界充满了崭新创造的例子,这些创造都是前所未有的杰作。但许多人仍宁愿相信天底下没啥新鲜事。作家劳伦斯(D.H.Lawrence,1885-1930)即对此深信不疑,一直到四十岁时,他才发现过去的想法是错误的。
我记得我曾经表示过或是曾经写过:任何能够入画的事物都已经入画了,在画布上的任何一个笔触都已经有人试过了;视觉艺术已经走进死胡同。然而突然间,到了不惑之年,我开始为自己画像,并为此着迷不已。我发现在空白的画布上,我可以为自己画像。这就是重点:在空白画布上作画。我一直到了四十岁才有这个勇气去尝试。
在创造的导向中,劳伦斯的发现实属稀松平常。它说明了原先看似死气沉沉的东西,突然间又生气盎然起来,是很可能的事。
首次进入创造导向的人,经常犯的一个错误,就是试图找寻自己所要的事物,好像这项事物是深埋地底下、亟待挖掘的宝藏。
这些人的方向错了。创造自己所欲并不是一个挖掘性的过程,也不是要你去寻找什么。但如果不是挖掘或寻找,那么它到底是什么呢?对于曾积极参与创造过程的人而言,无论从理性或直觉上来看,问题的答案都是显而易见的。这个问题的答案适用于所有的创造性行为,无论是创造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或是为电脑科学设计领先的科技,都是一样。
不幸的是,传统的教育制度常常漠视此答案的力量与重要性。但一旦开始运用此答案,新的创造力量和通达力将随传随到。